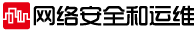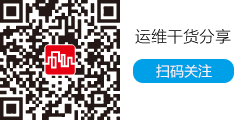“N+1”补偿方案
“新劳动法”即将实施背景下的大范围人事变革,华为并不是第一家。央视的大规模裁员早已走在前面,沃尔玛全球采购中心半数针对中国员工的“无原则解雇”裁员通告紧随其后。不过按照提供给员工的补偿额度排序,华为绝对排在第一位。
“沃尔玛的裁员是公司发展到一个瓶颈,面临困境,员工过剩,但华为完全不同”,在专业财经记者程东升看来,华为处于“非常好的发展时期,现金流非常充裕”。程东升凭借《华为真相》等书,树立起自己对华为的专业分析地位。华为的内部通报有更具体描述:“行业洗牌和友商重整”给华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会,“预计今年销售额将突破160亿美元”,“海外市场可望达到公司销售额的80%”,“产粮区开始从发展中国家覆盖到发达国家”。这或许正是华为能提供丰厚补偿的底气所在——据媒体估算,这次“集体辞职”的赔偿总额将高达10亿元。
对于赔偿,华为的说法似乎财大气粗:“即将生效的《劳动合同法》,对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有两个限制:一是补偿的年限不能超过12个月;二是高工资者,计算的每月工资标准,要以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封顶。由于没有这两个限制,我们的补偿方案要优厚于劳动合同法的标准。”具体赔偿方案辗转从华为内部人员那里流传出来,这份被称为“N+1”的方案,有一个计算方式:(N+1)×员工月补偿工资标准(税前),其中“N”为员工在华为连续工作的年限。“月补偿工资标准”不仅是员工的月标准工资,还包括员工上年度奖金月均摊值,此外还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
按照这个方案,华为的“变法”需要支付的成本,至少从数字计算上,并非简单地降低人力资源成本,至少从表象上,“从反方向实践了‘新劳动法’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新劳动法”的立法起点,就是倾向于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以法律约束来强制调整严重失衡的劳资关系,对于一般的企业,意味着低人力成本时代的结束。但“华为不是一般企业”,程东升提醒记者注意,这家1988年成立的民营企业,高速运转过程中,一直走“高薪”路线。用任正非的说法,华为就是“高效率、高工资、高压力”的“三高”企业,“高工资是第一推动力”。很简单的例子,知道“华为”这个名字的人很多,但细问起来,相信电信产业之外的人,九成以上完全不清楚这家高科技企业的具体经营项目,华为被许许多多不了解它的人记住并传播的原因很简单,和那些知名外企一样,是“一家高薪企业”。
“以物质文明来巩固精神文明,以一种机制来促使他们主观上为提高生存质量,客观上是促进革命,充分发挥他们贡献的积极性。”这是任正非的强调。1997年,华为从深圳坂田购买了将近2平方公里的土地,开始建设生产基地,包括生产中心、研究中心、员工宿舍等一系列配套设施,还有豪华而备受争议的行政中心。在一位华为前任海外市场高层的回忆里,这个现代化的生产基地,曾深刻震撼过他们的外国客户:“坦率地讲,我们一行之前非常希望见到一座‘电信血汗工厂’——那场景或许是在烈日下炙烤的一排混凝土建筑,其间装满围着印刷电路板忙碌的未成年劳工,一天工作18个小时,只有上厕所才能得到片刻休息。”
华为确实很注意自己的外表形象,位于深圳的华为坂田基地,已经成为外交部、商务部以及广东省与深圳市政府接待外宾的必经景点。华为曾强调,华为与中国绝大多数出口型生产性企业的根本差别在于,“华为不是靠大量廉价劳动力来赢取国际订单和外汇”。程东升对此做过细致描述:“技术研究及开发人员46%,市场销售和服务人员33%,管理及其他人员9%,生产人员12%”,“两头的研发和营销力量特别强大”——这是不到20年的时间,华为从1988年那个注册资本金2万元、没有背景、没有名气的小企业脱胎换骨的重要原因之一。
程东升仔细梳理过华为的大规模人才招聘计划,从1998年开始,“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主要媒体上大做广告,在著名高校里召开招聘专场,重金招揽各路高手”。1998年的第一次大规模招聘,华为曾与竞争对手中兴通讯在清华校园里上演过一场针锋相对的“招聘战”,凭借“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华为胜出。这一年“华为从全国招聘了800多名毕业生”。此后每年都有大量知名高校毕业生进入华为——“1999年,招聘2000名大学毕业生”,“2000年,招聘4000名毕业生”。2001年更是制造了一个轰动顶点,这一年,华为“挨个到全国著名高校招聘最优秀学生”,据说还口出狂言,“工科硕士研究生全要,本科的前十名也全要”。这一轮的华为合同招聘了7000多人,最后实际招聘了5000多人。借助这次被称为“万人大招聘”的全国最大规模的招聘,华为声名鹊起。这些学生在培训后,有80%以上充实到了研发岗位。累计下来,按照任正非的说法,“华为平均每年招聘大约3000人”。根据辞职风波之际的华为内部通报统计,“目前华为员工总数已经超过7万余人”。
华为数量巨大的高素质员工队伍,在企业福利逐渐完善过程中,显然存在巨大的成本压力。在潜在的劳资纠纷可能里,高素质员工,又成为在谈判桌前必须面对的群体,而“新法”框架之下,他们将被赋予更能自我保护的议价能力。从这个角度而言,“新劳动法”对于华为的挑战,的确与其他企业不在同一个层面。
闭合管理与闭合循环
高度知名而又极其低调,华为因为这种反差被认为是中国“最神秘”的企业。其实从不知名的小公司开始,华为已经有了内部规定,任何人都不能随便对外发表意见,这规定随着华为的扩张被益发强化。在程东升历时3年的采访里,“即使已经离职的员工,对于探听华为情况的来访者,也保持着高度谨慎”。他前后采访过的上百名华为人,最后都要求他“隐去真实姓名”。至于老总任正非,除了他本人在《我的父亲母亲》中的自述,没有任何媒体能提供他的私人信息。迄今为止,试图直接采访他的媒体都吃了闭门羹。任正非只是“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场合,抛出他一篇篇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并集聚了众多专家智慧的文章,与媒体进行单向交流”。
闭合管理与闭合循环,已经成为华为成功的某种保证。任正非这样强调:“华为经历了10年的努力,确立了自己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与企业的行为逐步可以自圆其说了,形成了闭合循环。因此,它将会像江河水一样不断地自我流动,自我优化,不断地丰富与完善管理。”在程东升的观察里:“华为的确有着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任正非的个人意志已经制度化为华为的管理体系和各项规章。1997年《华为基本法》的出台,已经显现了任正非不同于一般企业家的远见,程东升评价,他通过“基本法”的形式,“把企业思想的循环过程固化下来,形成动力机制”。任正非自己后来总结,起草《华为基本法》的目的是,“我们要逐步摆脱对技术的依赖,对人才的依赖,对资金的依赖,使企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彭剑锋是《华为基本法》起草小组专家之一,他回忆他和任正非交流的过程说,任正非是一个思维敏捷、极具前瞻与创新意识的人,经常会有一些突发性的、创新性的观点提出。随着企业扩张、人员规模扩大,企业高层与中基层接触机会减少,他发现自己与中层领导的距离越来越远,老板与员工之间对企业未来、发展前途、价值观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无法达成共识。这需要在两者之间建立共同的语言系统与沟通渠道。《华为基本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
专家组的第一份提纲并没有获得任正非的满意。一个月后,任正非和升任副总裁不久的孙亚芳飞赴北京,在北京新世纪饭店的咖啡厅中约见了专家组。任正非发表了他的诸多意见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会再度复兴”的观点,“在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中,知识资产使得金融资产苍白无力。按劳分配要看你劳动中的知识含量,按资分配正在转向按知识分配”。最后成文的《华为基本法》里这样表述“价值创造”:“我们认为,劳动、知识、企业家和资本创造了公司的全部价值。”关于“价值分配”的意见反馈里同样显现了任正非的想法,“基本法应当把创造企业价值的几大要素分离出来,每种要素怎么一个分配机制要说清楚”,“在价值分配中,不但是劳动,还要考虑风险资本的作用,要寻找一条新的出路,用出资权的方式,把劳动、知识转成资本,把积累的贡献转成资本”。这被认为是任正非关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会再度复兴”观点的延伸。
《华为基本法》出台后,华为立即敏捷地着手人力资源管理的调研。1996年到1997年期间,负责人力资源的副总张建国被多次派往香港考察几家著名的咨询公司,最终选择了一家美国背景的管理咨询公司——HayGroup,为华为做薪酬体系咨询。这家公司花了两年时间到华为做调查分析,以张建国为首的人力资源部也成立了一个有10多名成员的小组予以配合。HayGroup公司最终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那天,专家们从香港乘船抵达深圳,由于船舶误点,本计划21点到,最后一直到22点多才到达。第二天,咨询公司专家提交了方案,并与华为高管人员交流了不到一个上午,中午吃完饭就回去了。花了一大笔钱最终得到两个小时的讲解,华为还是觉得比较值得。张建国认为,“HayGroup公司提出的美国式的薪酬考核体系,关键是提出了新的管理理念和思路”。